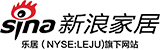吴健伟:深圳设计需要原创与文化底蕴(2)
二、我眼中的深圳设计行业,未来发展展望;
【主持人】什么时候开始有自主的设计?
【吴健伟】我是这样的,1993年的时候我们做设计的人来深圳,就是80年代末期来深圳的人,最早期解决的就是我最好是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住的小单间。
说这种小单间还不是你买,也不是你租,最好是单位给你分配一个单间,因为我们刚来深圳的时候,住的是工地,住的是铁皮房,就是深圳大剧院刮了台风把你的屋顶掀走了,然后你住在铁皮房里面一溜过去,墙没封死,隔着四间房子你打呼噜都可以听得到的,而且中午12点钟的时候,那个温度里面根本待不了人。所以,早期的时候,首先要解决一个生活状态问题。所以设计师当时比方你在公司上班,你只能充当一个绘图员,你的工资也就是每个月就那么可怜的几百块钱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想,在最快的时间内赚到钱改善生活状态,所以说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,这位先生是1993年来到深圳的时候,深圳的设计师就开始承包工程去了,刚才讲的中央工艺、广州美院的,他们就开始去承包工程,我们也纳入了这个行业这个梯队,就是承包工程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设计出身的人,他可能跟甲方交流沟通过程当中,甲方感觉会好一点,我们以前都是叫包工头,包工头农民出身,语言沟通人家就发现可能比设计师稍微弱化一点,所以在那个时候工程很好接的,一个500、600万的工程,三天就可以,就是第一天画平面方案,平面方案甲方说OK了之后,第二天就做一个整体的包干报价,第三天签合同,马上就打钱。所以90年代初期的时候,很多很好的设计师就开始去承包工程,成了一个施工的项目人。这个时候他们更多的经历是在周旋一个个工地上的管理甲方的攻关,所以非常的艰辛。因为设计师其实说实在的做管理还是差一点,所以有些人做得好,有些人做得非常失败。
因为管理是另外一个学科,为什么会有EMBA这个概念,你学设计的你就搞设计,做管理的就是管理,他是两个领域的概念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,到了90年代后半期比方说1995年之后或者1997年之后,来了一些70年代的新生的设计师,他们非常注重设计这个专项体,就是工程绝对不做,就做设计,你再大的业务我也不去碰,反而他们成功了。这一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杨邦胜,他绝对不做施工的,那个时候他在洪涛的时候,很好的业务可能有一个1000多万的马上可以成交,马上可以给你预付200、300万,能够挡得住这种诱惑,然后孜孜不倦地在做自己的本项专业。
【主持人】纯粹做设计?
【吴健伟】对。
【主持人】后来还可以收设计费了。
【吴健伟】其实这个设计行业的大环境慢慢地在向一个比较规范化、比较受众于广大百姓的认同这种基础上,我们90年代初期有一种奢望的心情,他知道设计是要付费的,以前90年代时候什么装修设计还要给钱,还要给设计费,不都包在工程里面吗。现在确实有很多业主,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他生活到了一定的高度,一定的品位,他对他生活的东西有一些追求,所以他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,才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设计。当下的情形相对来说要好很多,实际上准确来讲,我个人认为,设计费开始收的状态下应该是在05年之后这个气氛慢慢地浓烈起来。
【主持人】就是说之前设计师地位还是没有现在这么高。
【吴健伟】对,这个也是因人而异,有些人他可能把控得比较好一点,或者借助于一些外界的力量,如果你是纯粹的本土的深圳的设计师,你想去收一个费,或者是收很理想的费用比较难,他可能借助香港或者台湾的然后大家打包整合起来的。
设计收费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,我有一个案例,在1994年的时候,我有一个朋友介绍了福州的一个五星级营酒店―邦辉大酒店,就要找设计师,后来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我,我想如果是我们深圳这样单枪匹马冲上去的话肯定不行的,我在最快的时间内和香港的一个朋友在香港注册了一家设计公司,就拿那个香港设计公司就把五星级酒店的设计合同签下来了,当时的设计费是380万,这个设计让我在一些从事设计行业的朋友哇,羡慕得不得了。
【主持人】当时是一个比较天价的费用。
【吴健伟】最重要的就是你作为一个设计师,你能够挣那么多钱,本土出身的一个设计师,能够签了几百万设计费的,真的,这个说起来大家都觉得哇,真的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想当时是借助香港朋友,我当时找了香港的一个朋友注册了一个香港昆仑国际设计公司,马上做了我们的平面设计的概念出来,做了一个概图出来,推上去,当然也是靠我们在现场跟那个业主的交流沟通,把他一些关键点给抓住。所以说设计费这个问题其实按照目前的时期,我觉得我们现在设计行业相对来说,在这个设计费上面还比较牛了一点,比方说我就是600块钱一平方,假如你不找我,行,你可以去找一些其他人,也有便宜的,没关系,已经到这个份上了,我觉得未来还是蛮美好的。
【主持人】深圳设计和全国比较,现在还有优势吗?
【吴健伟】纵观全国设计界的区域的划分,其实我个人理解深圳的设计落后了那些城市。首先我们讲中国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上海、北京,我们看上海的设计包括北京的设计,包括他们那些我们不讲是国外设计师做的,就是国内设计师做的东西,都已经非常棒了,包括西安,包括福州,包括长沙。他们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很重的文化底蕴,他们所设计的东西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。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就是他的专业化,就是他的造型的专业化,色彩的专业化。
【主持人】有文化,并且更专业一点。
【吴健伟】对,我认为这种环境造成的这种原因肯定是多方面,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业主的参与,就是说我们广东深圳这一块,人家说早期有一个词叫“文化沙漠”,现在为了让这个词义渐渐地淡化,所以深圳市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,做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节、艺术节,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场所,各种各样的供市民来融入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生活方式都在改善,这是硬件方面的东西。但是真正的整个市民层这一块的他们的文化底蕴、文化追求相对要弱了一些,比方说我们讲到文化氛围,深圳市民整个发展的历史30年,你的大学的教育,你跟内地城市比起来,那就是差了100年的概念。就说我们武汉,我是武汉人,武汉的大学以前没有合并的时候是100多所,现在合并了还有75所。深圳翻来覆去就是这些,所以他这种文化底蕴所产生的那样的一个项目,上一次设计行业协会赵秘书长说一个概念我非常认同,我们要评出一个“最佳业主奖”,意思就是在设计师做的这个项目中,业主是全力支持、全方位支持,这种气氛这种火候在内地城市做得相对好一些,就是让设计师能够把他的设计创意,设计的原创的东西和一些设计的理念不说100%,能够达到90%以上实施到项目当中去,就保障他设计的效果氛围就不一样。所以相对而言,我们对内地城市的有些项目确实感动,有的时候甚至是惊讶,包括我们广美以前的同学校友,他们去到北京做了一些案例非常的有底蕴,我们叫“底蕴”。
【主持人】吴老师您觉得现在国内的室内设计师中还是有大师的是吗?
【吴健伟】室内设计师我是这样想,就像我个人认为,我们广美的李雪玲(音)应该也算是。因为所谓大师,他可能把商业的东西放得很淡,包括浙江美院的那边有一个,他们现在都做设计都做案子,做案子的同时还做一些学术性的探讨研究,其实我个人的情结非常关注设计师领域他们这样一种生活方式,他们那一种互动。
我们深圳市场氛围是最好的,就像刚才讲的,看见一个什么项目投标,哗哗一去,50%的都是深圳公司,这种历史我们都经历过,我们应该是在七年前都经历过这些事,我们叫“效果图大战”,每家公司为了一个项目,分头去做效果图,做完之后那个时候还不是用投影的,全部要打印出来,打印出来还要装裱,然后就每一家公司一摞一摞的都是往北方扛,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扛到大连去了,一去,深圳的那一天就有四家单位全部扛着效果图去参加投标“选美会”,但是后来我们从03、04年之后,凡是投标绝对不参加。
因为他这个就是跟装修公司是衔接在一块的,我们从90年代做工程,后来慢慢醒悟到了不能做工程,那得纯做设计。所以纯做设计了,因为投标那里面一定是工程投标,设计哪有投标的,设计有投标但是保底费要很高我们就去。比方说一个五星级酒店,你给我50万保底费,OK,我跟你去,你给10万块钱保底费,我相信做到一定份上的都不会去。你比如说像奥运会场馆一个鸟巢保底费是200万,OK,他还要选你,你说我也参加,不行,我不让你参加,就是五家国外的设计公司来做。
所以谈到大师的概念,我觉得中国肯定还是有大师的,不是没有大师。但是这些大师他往往没有那种商业化,比方像我们前期的陈逸飞应该也是大师。陈逸飞他画画得好,油画很出名,他也是做室内设计的,他也做过很多的项目。还有我们知道的陈丹青,陈丹青原来也是油画出身的,他也做室内设计。现在人家开始玩文化了,玩文字性的游戏了。还有我们认识的艾未未,艾未未也是个文人,他也做城市设计。我们北京的鸟巢那些那种中标的那些公司把他请去当顾问。
所以说中国的设计情结他有一个矛盾的地方,就是说经济状态和专业状态你怎么样去杠杆平衡的问题。深圳这一块我个人认为,经济氛围比较重一些,北方的特别有一些玩另类的设计,就是说玩自我的,他就会把钱我是要赚,但是我到了一定的时候OK了。所以我们讲深圳的设计师,我们认识很多,非常有名的设计师,开的车子都是100多万的。咱们看到北方的很多设计师他不会是这样的,所以有很多情结,这就是我讲的一个设计专业和经济收入这个方面的权衡的关系。如果再谈到新生设计力量也好,其实我个人认为,深圳是新生设计力量非常多,像我们确实年纪比较老的。所以说感觉压力很大,现在年轻的设计师非常有冲劲,因为80后的孩子,他们的成长教育,他们主张的这种个性的张扬,其实我也有受感染,虽然我已经快50岁了,但是我在想我自己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一些比较跳跃式的思维。